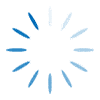被欺负狠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停下的时候,阮序秋的身体还在不受控制地发抖,腿心的整个阴部红肿无比,阴唇与嘴巴一同张着翕合着吐出汩汩的浊液,密密麻麻的吻痕犹如凌虐。她整个人动弹不得地保持着张开双腿的姿势,像个搁浅的鱼一样断断续续地喘着气,神志不清地看着应景明,无意识地流着眼泪,心里想:「身体……好像已经坏了……」
应景明是个混蛋,所以当她听见阮序秋这么想的时候,听见阮序秋要死一般奄奄一息的心声,她再次狠狠地要了她一回。这个地步,已经无需任何束缚,她只需吻她,然后进入她,毫不留情地吮吸研磨她的敏感点,无论多么用力,多么极致,这个人也已经做不出丝毫地反抗挣扎。她依然好似乖巧地软着身体,连向上躲避的力气也没有,只能彻彻底底地承受着全部,爽得浑身痉挛的同时,发出崩溃无助的哭声。
淫靡的情欲中,应景月的话不断在应景明的脑海中回响,“我才十六岁,最多只是乱亲人而已,怎么可能见人就上啊……”
“这也太丢脸了,整天说着海妖海妖,结果还是个雏,可偏偏我就是不敢嘛,那种色情的事情……”
好像试图阻止什么,可是她已经无法停下,自以为洁身自好的她已经爱上了这种感觉。
应景明在奇怪的羞愧与痛苦中不断深入占有,直到高潮为止,触手的吸盘中射出一股液体,一切才终于结束。
做了太久,一夜就变得很短,好像刚睡下,天就亮了。
而就是这种情况,第二天,阮序秋依然准时出现在学校。
早自习碰到她的时候,阮序秋还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然后强装无碍地离开。
但应景明知道她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才让自己的走姿看上去跟往常一样,事实上,如果不是海妖的体液保护了她,别说下不了床了,可能得去趟医院才行。
“这自制力,真是让人不服不行。”她不住咂舌摇头。
愧疚么?没有那种东西,不过早操被她当着学生的面批评懒散的时候,她没有反驳,而是乖顺地认错;被她差遣跑腿的时候,没有怨言;给她送午餐,被责骂不合胃口的时候,也只是笑笑而已,然后按吩咐再去买一份回来。
当然,并不是她突然转性,因为跑操时的懒散是故意的,给她跑腿送文件是主动的,当然午餐也是故意买不合她胃口的饭,然后笑着看她发脾气。
小情趣嘛,昨晚确实过分了,被骂两句也是应该的,尽管在旁人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都以为她又被针对了,一个个学生为她抱不平,这不,就连阮明玉都来安慰她,说:“应老师,你别生气,我姑姑她就那样的,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啊?哦,我没生气。”应景明笑呵呵地回答。
“不过虽说刀子嘴豆腐心,但伤了人也是真的,是我姑姑不对。”
应景明哭笑不得,“明玉,你误会了,我真的没有生气。”
阮明玉闻言,用探究的眼神看了她一会儿,片刻注意到了什么,视线看向她的手腕,转了话锋道:“手表,老师不喜欢么?”
“手表?哦,那个啊……”
“老师,你没有拆礼物?”
“拆了,我拆了,但是因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戴了。”
“哦,好的。”她低下头去,似在想些什么,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才抬起头,“我先去上课了,”
“嗯。”
晚上,应景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表戴上。
那是一个普通的银边皮带手表,简约的商务风,看上去并不廉价,但是鉴于这是学生送的,应景明想,应该也不会很贵。如果贵的话,那就可能是阮序秋授意的。那个家伙口是心非,心里指不定多感激她英雄救美呢。
戴上看了看,还挺衬她的衣服。
不过这到底是她第一次戴手表,总感觉手腕被什么东西勒着、贴着,难受,连黄片都没心情看,最后趁着片尾曲的空档赶紧摘下来,想着明天出门再说。
“怎么了?”一旁的阮序秋注意到她的动作,低头看了一眼,“你什么时候开始戴手表了?”
“就是还没开始啊,”她笑着取下来,被阮序秋接过去,“戴不习惯,可能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阮序秋左右打量着,“什么时候买的?”
“前几天明玉送的,”应景明答,“我还以为是你让明玉送给我的,啧,原来不是啊。”
阮序秋一愣,又看了看手表,脸色一变,立马还给了她,“我送你手表干嘛?”
“你这个当事人倒是没有一点表示。”
“我要表示什么?我说了谢谢了,也肉偿了。”
应景明漫不经心地笑,“什么肉偿,我们是炮友,那是相互的好么?”
她满脸涨红,“你都快把我弄死了,也叫相互?”
“要是你心里想我温柔,我也可以温柔,可是你明明就喜欢得要死啊。”她忍俊不禁地面对阮序秋益发恼羞成怒的脸色,玩笑般与她僵持了半晌,直到少女的呻吟在寂静的客厅中响起。
她看向电视,“不说了,开始了。”
阮序秋瞪着她,不时,愤然起身,“不看了,我要回去。”
应景明拉住她,“诶,第三集可精彩了,你确定不看?”
“我要回去。”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
她的神色看上去很认真,眼睛甚至都有点红了。
阮序秋是真的生气了,应景明突然意识到。她连忙关了电视,将她拉回身边坐下,手臂环住她的背,“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
阮序秋也不说话,光是暗自咬着嘴唇,黑框眼镜下的一双眼珠子又湿又倔,像被欺负的小土狗。
然后,眼泪就掉了下来。
天知道,就算加上酒吧那次,这也仅仅只是她第二次看到她哭。
应景明一面手忙脚乱地给她擦眼泪,一面道歉,“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无论我说了什么,你千万别生气。”
她是真的有些急了,她知道这个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以咬嘴唇的方式克制情绪的,她觉得咬嘴唇显得脆弱,因此以往在她的面前,就算咬碎了牙根,顶多也只用抿唇化解心中的焦灼,然后十分体面地平复情绪。
有这么严重么?她刚才说了什么?肉偿?还是炮友?算了不管了,“我真的错了,你要我怎么道歉都行。”
可是越哄,阮序秋就哭得越失控,摘了眼镜,她整个上身都蜷缩在一起,脑袋也越埋越低。应景明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将她抱住,然后一遍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这么多年,明玉从来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哭了半天,阮序秋哽咽地道。
抚拍她背脊的动作顿住了。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