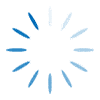不过几息,楚瑜的嘴里只剩下喘息和呻|吟,再也没有吃点心的闲心了。
难得放纵,与心上人不过毫厘,借暑气三分,搅作满腔火热,一发不可收拾……
日落西沉,风猛地将窗子推起,发出不小的声响。
“嗯……”楚瑜睡梦中闷哼一声,全身酸软,只能动了动指尖。
秦峥正给他擦身子,听见动静回头看了眼,轻轻摸了摸楚瑜肩头,柔声道:“没事,起风了。睡吧……”
楚瑜闻言舒展了眉头,沉沉睡去。
秦峥将手里的帕子搁在一旁,取了蚕丝毯给楚瑜搭在腰腹上,这才起身去关窗子。
外面当真是起了风,树枝乱颤,风雨欲来。
※
忽闻雷声平地起。
一滴冷汗聚在眉心,顺川壑滚落,隐于鬓。
梦里不知身是客,却见眼目的血色翻滚,烛泪层层叠叠,入耳俱是一声接一声的嘶喊。眼前的光一点点散去,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最后消磨去所有的希望。躺在床上的人像是断了根的枝叶,直到所有的呻吟变得声嘶力竭。
绝望,乞求,卑微,直到俱作灰烬。
裹住婴儿的襁褓只留下一角,一只青白的小手漏出,腕上一抹朱砂痣,殷红。
“秦峥——”
楚瑜猛地坐起身,原是梦一场。
隔着云丝轻纱,瞧见外面天色已晚。
又是一声惊雷,楚瑜蓦地回过神来,身旁已经没有秦峥的身影,空落落的枕,空落落的床。
心里忽然塌了一角,楚瑜眸中瞳孔一紧,撑着床榻起了身,连鞋都顾不得穿,失魂落魄的推门出去,外面竟已暴雨如注。
秦峥擎着伞,面前站着几个将士,似在说些什么。他回头,隔着雨幕瞧见楚瑜扶着栏,站在门前。
“清辞!”秦峥大惊,手中伞滑落,他几步飞奔到楚瑜面前。
楚瑜扶栏,缓缓抬头,脸上尤有泪痕,眼尾泛红。他身上只穿着单衣,长发垂散,苍白的脚踝下赤着一双脚……
“清辞,你怎么了?”秦峥心头一痛,打横抱起楚瑜往屋里走。
烛台已点上,楚瑜身上披了长袍,他坐在床头,不声不响。
秦峥从外面端了热水放到楚瑜面前,他跪下身子,伸手试了试水温,这才轻轻握住楚瑜脚踝放在盆里,缓缓揉着。
这双脚仍旧苍白,只是因着胎位下降有些浮肿,秦峥按揉着,轻声问道:“又做噩梦了?里衣都湿透了。”
楚瑜点了点头。
秦峥叹息,语气里满是宠溺的责备:“那也不能乱跑呀。”
楚瑜没说话。
“下次做噩梦了就大声喊我。”秦峥抬眸,认真道。
楚瑜伸手,轻抚住他脸庞,道:“我曾在山中古刹修行一载。”
秦峥一怔,他从未听过楚瑜礼佛,若有过恐怕便是那年他离京之后了。
楚瑜似回忆当年,轻声道:“此诸痴猕猴,为彼愚导师。悉堕于井中,救月而溺死。明知是无妄,偏要盼着一取水中明月,爱一人是否当是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清辞,我参不透佛偈,却知人生在世,白驹过隙,爱我所爱之人,惜我所惜之事。不可一朝风月,昧却万古长空。不可万古长空,不明一朝风月。”秦峥长长叹息一声,用棉帛将楚瑜脚上的水珠擦干净,放在榻上。
楚瑜垂眸,长长的睫毛遮住眸中神色,似在思索什么,许久,忽然抬起头来,似悲似喜:“是,是了……昨日已过,命已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秦峥笑,眼底却有泪:“清辞,谢你初心……”
孰无错,孰无过,众生皆苦,诸行无常,初心不忘,应作如是观。
夜深,雨声喧然。
秦峥看着怀里已经熟睡的人,轻轻弹指熄了烛火。
愿此后再无梦魇傍身。
楚瑜醒来的时候,秦峥已经走了。
帘外雨潺潺,他倚在窗前的榻上,手里捧着一只白玉小碗,慢条斯理的用指尖汤匙搅着里面熬煮精细的糯米粥。
听着常平的汇报,楚瑜心里有了数。秦峥不该走的这样急,往常就算是有事也总会等他醒来同他说一声才会离去,免得自己醒后寻不着他。若走的这样匆匆,只怕是前线又要打仗了。
想到这,楚瑜心里不免发紧,窗外的雨丝如帘,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常平伸手将窗子合上,阻断了楚瑜的视线,不等楚瑜表示不满,抢先道:“外头风大,您坐这儿窗边,若是淋了雨可怎么是好?”
楚瑜没法子瞧外头雨景,只得悻悻叹道:“你这张嘴,愈发厉害。”
常平垂眸笑的腼腆:“二爷宽容,别与我们几个计较,若是照顾不好二爷,回去秋月姐姐免不得要收拾我们几个。”
提到秋月,楚瑜又想起远在上京的真儿,他将手里的白玉小碗搁在一旁,从常平手里接过帕子擦了擦指尖,道:“磨墨。”
给女儿的家书,纸要用桃花笺,墨要用松烟墨,笔要用紫毫笔,家书后要附一张真儿的小像,最好还能描朵花儿上去……
字里揉了几分雨声,墨香淡淡萦绕,常平几次想提醒楚瑜不宜久坐,可瞧见自家二爷垂眸书写的认真模样,又不忍心打扰,只能在一旁候着。
楚瑜一手楚家笔体书的颇有韵味,落纸云烟,行云流水,只是临到末尾忽然笔锋一顿,一团墨顺着笔尖低落,晕了桃花笺。
常平心里咯噔一下:“二爷?”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