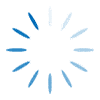她也不会,遇见后来所珍惜的一切。
柳拂嬿抬起手,掌心温热,握在他攥紧的拳头上。
“阿韫,我告诉你这些,其实是想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比起它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男人抬眸看她,哑声问:“是什么?”
柳拂嬿笑着道:“是你让我不再恐惧与人接触,让我接纳了自己的一切,包括我的恨,我的爱,我的这颗痣。”
“也是你,知道我的所有,见过我的一切。”
“所以——”
她坐在窗下,微微偏过头。
玻璃上结着晶莹剔透的霜花,红色的剪纸映着窗外的雪光,温暖地流淌在她的眼睫上。
那双记忆中清冷又疏离的长眸,不知何时早已霜雪化尽,像春江花月那般温婉明亮。
她嫣然一笑,像一场雾气散尽的清晨,曙光乍现的初晓。
嗓音里,也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
“所以,我已经彻底痊愈了。”
-
今年的冬天好像比以往更温暖一些。虽然积雪未化,街道上还是人来人往,极为热闹。
情人节前一晚,陶曦薇打来电话,说自己很紧张,希望柳拂嬿陪她度过这段忐忑时光。
原话是这样的:“主要也不知道,某个狗男人会不会叫我出去约会。”
“不过我在装行李。”柳拂嬿把手机放到支架上,“可能没空一直坐在手机前面,戴着耳机陪你可以吗?”
“大晚上的,你要去哪?”陶曦薇问。
“去巴黎。”柳拂嬿看了眼时间,“再过两小时上飞机,睡一觉醒来,应该就到地方了。”
“天哪,跟你老公去过情人节?”
陶曦薇比了个大拇指。
“太浪漫了,都老夫老妻了,还搞得这么有仪式感。”
柳拂嬿给她纠正:“我们是新婚夫妻。”
戴上耳机,她继续翻箱倒柜,在找护照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本眼熟的白色封皮文件。
柳拂嬿指尖一顿,把它拿了出来。
这是之前和薄韫白签过的那份合同。
就在那个秋天的夜晚,他把自己那一份丢进了碎纸机。
柳拂嬿当时还不确定后来会怎么发展,保险起见,她并没有销毁自己这份。
现在再读那些冰冷又生硬的条款,只觉得有点好笑。
真香可能是人共同的天性。
她将合同重新放回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去书房,一并把它碎掉。
回想起当时签合同的心情,简直有些恍若隔世。
不过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确实挺愉快。
虽然她当初说出上述憧憬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意思。
望着这个东西,柳拂嬿稍微走了一会儿神。
过了阵,才被耳机里陶曦薇的声音唤了回来。
“喂喂,嬿嬿,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在听在听。”她赶紧道,“怎么了?”
陶曦薇也没怀疑,接着道:“反正就是我这次回家,我妈给我塞了好多家里那边的好吃的,叫我带给你。你什么时候有空哇?”
“等我回来吧。”柳拂嬿弯了弯唇,“你记得替我谢谢孙阿姨。”
“这有啥好谢的。”陶曦薇毋庸置疑地截断了她的话头,“咱俩什么关系。”
本以为她还要大聊特聊一场,结果这个本以为会持续很久的电话,在十分钟后就迎来了结束。
“我不跟你说了啊,”陶曦薇匆匆摆摆手,“钟俞给我发消息了。”
柳拂嬿还在思忖是“钟俞”还是“终于”,结果就这样错过了吐槽的最佳时机。
一句重色轻友还没说出来,听筒里已经响起无情的嘟嘟声。
少顷,听见身后有人敲门。
回过头,就见薄韫白不知什么时候起已经站在那儿了。
天气渐凉,他穿了件黑色的高领毛衣,愈发显得脖颈修长,肩宽腰窄,比例绝佳。
其实这衣服柳拂嬿在广告上见模特穿过,那么一张混血神颜,穿起来也就平平无奇。
偏薄韫白的身形是天生的衣架子,什么都能毫不费力就穿得好看。
男人抱臂倚在门边,乌发低垂,眸底光影明灭。
嗓音懒淡,问她:“打完了?”
“嗯。”柳拂嬿有点惊讶,“你怎么过来了?”
“别人能占用你,我就不能占?”
似乎等得有些久了,薄韫白唇畔并无一贯笑意。
他走进来,也在床沿坐下,不由分说揽过她的腰。
“想和老婆多待一会儿,不是人之常情?”
“是是。”柳拂嬿像哄学生似的哄他,然后才道,“不过能不能等一会儿?我东西还没收完……”
被他这么一抱,柳拂嬿够不着行李箱了,还没装进去的画具只能捏在手里。
“我帮你装。”男人接过那盘画具,漫声道,“你坐这指挥我。”
柳拂嬿其实不大会装行李箱,往往去的时候还能装下那么多东西,回的时候就装不下了,只好硬塞。
没想到薄韫白一接手,也不知道他怎么仿的,箱子里每个功能区瞬间分得整整齐齐,一目了然。
小小一个行李箱,就在她眼皮底下,变得跟多啦a梦的口袋一样能装。
衣服、素描本、化妆包、洗漱用品等装好后,薄韫白转身问她:“还有吗?”
“……”
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柳拂嬿抿了抿唇,就这样直视着他,然后坦坦荡荡地开口了。
“有的。”
“还有内衣。”
听到最后两个字,薄韫白隽冷清矜的眉宇碎裂一道缝隙。
他的神态倒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站姿也仍是那副散淡随意的模样。
但这句话说完,房间里的氛围忽然变得暧昧起来。
柳拂嬿背过身去,打开衣柜内层。
尽管也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反正,他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她小声道:“正好你在。我没想好带哪几套,你也帮忙挑挑看?”
柜门打开,几抹冷调的颜色映入眼帘。
淡白、烟青、银灰、纯黑……
都是那种没有繁复蕾丝的款式,简约却愈显高级。
薄韫白二十九年的人生里,并不曾见过这样的东西。
他在大开的柜门前沉默一瞬,一时有些分不清,她到底是诚心让他帮忙参谋,还是有些暗戳戳的别的心思。
“……这样挂着,我也看不出来。”
稍顿,男人垂眸看她。
“等你穿在身上,我才知道。”
“穿在身上?”
柳拂嬿错愕一瞬,眯了眯眼,眼尾那颗朱砂痣十分冶艳,明亮得毫不遮掩。
她凑近薄韫白一步,低声道:“现在就穿,还赶得上飞机吗?”
-
事实证明,自家的飞机不用赶,多等一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
夜色浓沉,飞机直入云端。
经历一场缱绻旖旎,柳拂嬿浑身发软,也就不太爱动,裹着薄毯看向窗外。
以前,每年画展频繁的那几个月,她也没少连夜飞过外地。
但那时都独来独往,吃饭随便对付,一上交通工具就是补眠。
不像此刻,薄韫白也在飞机上,两人同行。
而且,一想到飞行的目的是出门约会,心情也变得不太一样。
柳拂嬿不自觉弯起唇,感觉黑蒙蒙的夜空也明亮了许多。
然而不多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她又赶紧收了笑意。
少顷,薄韫白端着一碗东西过来。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