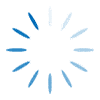第91章 番外·孩子(二)
◎储君◎
封弥今年五岁了, 每年爹爹和娘亲都会带他在哈赤住上小半年。
他喜欢哈赤,喜欢这一线苍苍的平野,喜欢这旷达彪悍的民风, 也喜欢钢筋铁骨的哈赤大将,每日都和爹爹在大营后练箭, 但今日的心情格外不一样。
“爹爹, 我头疼。”
咻!小芒弓搭着的短箭笔笔直地扎进了三丈远的靶心, 晃悠了两下, 终归是没有掉靶。
“站直。”
咻!长箭破空而出,一道银灰色策风而去,宛如冲刺的游龙, 眨眼间便没入了百步开外的箭靶上,一声巨响后, 靶子应声而裂。
封弥腰板挺直, 把小芒弓一背,鼓着掌叫好, 白灵摇头摆尾绕着封弥汪汪叫。
“头不疼了?”封暄垂下手,正好摸摸儿子毛茸茸的脑袋,再一视同仁地摸摸白灵的脑袋。
“疼的。”封弥攥着爹爹的衣摆,很努力地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 小脸皱成一团。
“吴青山就在哈赤,回头让他给你瞧瞧。”封暄简直没眼看。
“神医不行的, 听人讲,这叫心病。”封弥信口捏来。
“心病怎么疼到脑袋上去了?”封暄忍着笑,小不点儿, 还晓得心病。
“……”封弥一时也没转过这个弯来, 事实上他连心病的抽象指代都不知道。
“箭术学得不错, 糊弄人这事就别跟木恒叔叔学了,他还不如你。”封暄戳破了儿子的小心思。
眼看回京势在必行,留在阿悍尔成了一年复一年的大梦。
封弥的脸登时垮了下来,垂头丧气地飙了一箭,这回没装相,动作利索得很,短箭爆了点儿破空声,没入箭靶靶心的一刹那,挤掉了先前软趴趴的箭矢。
这一箭才是封弥的真本事,这小子为了不回京城,方才跟他爹装病弱呢。
五岁的小豆丁,就已经晓得要装得周到些。
七月的天还热,小褂子先穿起来了;头发睡得乱糟糟;脸上扑了点儿灶灰;往常活蹦乱跳,今日走几步就撒娇要抱,等爹爹抱起了他,便左扭右转地,恨不能把那一脸“憔悴病容”堵在他爹脸上。
“乖了。”
封暄翻开手掌,封弥正正好把脸蛋往爹爹粗糙的掌心里蹭,小兽似的撒娇,蹭个没完,一头短短的小卷毛在风里乱翘。
这小子心太野了。封暄想。
绿野一线连天。
司绒从草浪尽头走来,远远地就看见了一高一矮立着的父子,封弥蹭完脸,余光瞥到一点儿红,登时转变战术。
可怜巴巴地扒着爹爹的裤腿,眼泪止不住地往那裤腿上抹,嚎得震天响。
“一哭二闹三跳河没有用,”司绒把缰绳交给易星,“你先跳河,再闹,最后哭,更没有用,你娘亲是铁石心肠,回了京就卷卷你的小铺盖,去南匀书院。”
“小水沟也不叫河,半夜三更敲锣打鼓在城东挂上你封弥小皇子的旗帜也不叫闹,往爹爹裤腿上蹭口水更不叫哭,”封暄补充,抬手把司绒头顶的碎叶拂下来,“怎么是走回来的?”
司绒捂了下肚子:“不大舒服。”
“……”封暄紧紧罩着儿子的耳朵,偏头严肃,“昨夜顶着了?”
“?”司绒眼角飞红,在儿子的耳朵外边又罩了一层,“许……是吧。”
“回去揉一揉,乖了。”封暄哄儿子哄习惯了,对上司绒也是一种绝杀。
司绒看着儿子的后脑勺,微侧过头,封暄俯首下来短促地亲了一口。
小封弥的耳朵被爹爹娘亲的手捂得严严实实,习以为常地自个儿再捂一层,他心里明镜似的,爹爹娘亲要先说话,再亲,最后才会抱他。
“转过来吧小子。”司绒揉揉儿子的头发,这一头小卷毛又软又蓬松,手感好得不得了。
“娘抱。”他把小芒弓解了,张开手。
司绒笑笑,一弯腰,抱起封弥刚“啵”了一口,小腹就传来阵阵闷痛。
封暄当即拎起儿子后脖领,扛在肩上,扭头吩咐九山:“去请吴青山。”
*
天边滚来闷雷,草浪窸窸窣窣地一重推着一重,整片天穹都被染成了铅灰色,一条冽冽电龙骤然翻涌而出,搅风弄云,豆大的雨滴猝不及防地砸落迸溅。
封暄关上了窗。
屋里搁着冰山,吴青山阖着眼,须臾,神情有些凝重:“换手。”
司绒看了封暄一眼,奇怪的是,两人都怪紧张,递给对方的却都是安抚的眼神。
雨点急促地敲打在惊鸟铃上。
片刻后,吴青山收了手,欲言又止地把司绒和封暄看了一圈,最后一指头定在角落的冰山上:“这东西不好再搁这么近了,放到外间去刚刚好。”
这话一出,两人都愣住了。
“神医爷爷,为什么要放到外边去,这多热啊。”只有封弥一派天真地问。
“因为,”吴青山背着药箱,撩开珠帘,回头笑道,“你娘,还有你娘肚子里的小娃娃不能受寒。”
小娃娃。
司绒看着封弥的圆胳膊圆腿,再看自己的小腹,有那么两三息的时间没反应过来。
封暄笑了一声。
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涌动在窗纸上的电龙游光,用力搓了把脸,唇角越扬越高。
而后猛地转身,像个毛头小子似的抱住了司绒,一手轻轻地抚住她小腹,一手罩住她的脑袋揉搓。
第一句话问的是:“饿不饿?”
这完全是记忆作祟,司绒第一次怀孕那会儿,口味混乱,从前爱吃的半点儿不想沾,反而好吃些味道稀奇古怪的东西,封暄对此印象深刻,往往陪吃一次,就要斋素三日,否则无法驱除那恐怖的味觉折磨。
可说实在,司绒自己都有些记不得怀封弥时是什么感觉了,听阿娘讲,女子会自然地忽视遗忘怀孕与生产时的辛苦,她如今只记得些大概,封暄倒是能把细枝末节娓娓道来。
这夜,他从上锁的红木箱中取出一只匣子,里头叠着两本册子,他翻出了压底的一本翻看。
当年封暄头回当爹,拿出治国安邦的势头,极为认真地翻阅医书、垂询太医,甚至逮着那些孩子养得好的大臣,旁敲侧击地询问经验。
他都一条条地记下来,包括司绒怀孕来的变化,通通拟成了册子,成为全天底下独一无二的记录,这事儿司绒都不知道。
*
回京计划搁置,原要拔营归京的天子卫队原地戍守,俩人决定在哈赤生下这个孩子。
哈赤已经今非昔比,从牵制南北的战略要地,一跃成了超越京城的巨大城池。从哈赤草原往北拓展,包含邦察旗,往东延伸,将东面万里平原也囊括在内。
句桑的孩子日渐长大,新一代的权力更迭即将来临。赤睦大汗有先见之明,先将阿悍尔作了内部划分,阿悍尔十六旗中,十五旗归句桑。
邦察旗以及邦察旗往北的长横草原归属司绒,地皮不算什么,长横草原底下流淌着草原的黑色血液,那是如今这世道上最炙手可热的东西。
所以,哈赤是司绒在八年间最大的心血,这座城是她的。
草木一度枯荣,眨眼便到了第二年春。
浴池里“哗啦啦”地传来笑闹声。
封暄才带儿子跑马回来,封弥今年有了第一匹小马驹,正是新鲜时候,他没让第二个孩子带来的变化影响到儿子。
每日读书练字、打拳习箭、跑马沐浴都是爷俩一起的。
司绒站在桌旁写信,正在把要务都分派下去,封暄抱着湿漉漉的儿子出来了。
“怎的还在忙?吴青山说你要多歇息,先搁笔,一会儿你说,我写。”封暄说着话,折身到屏风后去拿封弥的小短衫小袍子。
“你别惯他,”司绒头没抬,都能想象到封弥赖着爹爹不肯下来的模样,“衣裳穿不好便让他光屁股。”
小封弥咯咯地笑,光溜溜的,在爹爹怀里扭着身子,朝娘亲吐舌头。
“啪”一声,封暄往这臭小子屁股上拍了一下,丢给他几件短衫绸裤,“穿不好,等着光屁股。”
“……”封弥没想到爹爹倒戈得这样快。
“今日累不累?孩子闹你吗?”他爹已经绕到了长桌后,轻轻抚着司绒的肚子,埋首在她颈间深深嗅了嗅。
“不闹,乖着呢。”司绒说。
“嗯。”封暄像一只索求抚摸的大猫,蹭着司绒的侧颈,时不时咬两口。
司绒搁下笔,微微叹了口气:“求求你把衣裳穿上。”
“热。”
封暄就说了一字,便收了手,赤着上身坐在桌旁替司绒把没拟完的折子写好,归置完放小竹篮。
三四月的天,哈赤春芽都没冒,跟“热”字搭不上边,他这是燥的。
司绒今年二十六,岁月对她格外优待,仍然像一朵饱满润泽的鲜花,近年由于掌权的缘故,那明艳张扬都变成了不可直视的威信。
八年了。
人常说七年之痒,封暄看着她,心底确实有蠢蠢欲动的痒,它经年存在,并源源不断,变成一种只受司绒牵引的爱欲。
“娘亲,今日你过得好吗?”
封弥自己把小卷毛擦干了,乱糟糟地顶在脑袋上,正扒着屏风瞅爹娘。
他最近不知跟谁学了一句,日日逮谁都要问一句“过得好吗?”
至于娘亲,那是一日要问十遍的。
“好极了,”司绒没敷衍,掰着指头数,“吃到了酱鸭、霜酪,走了半个时辰,城务一切顺利……你怎么不出来?”
“妹妹今日乖不乖?”封弥不好意思说,他的小裤衩卡住了小鸟儿和蛋。
“乖。”司绒看出来了,扯了一下封暄,儿子平素和她亲,但已经到了初具羞耻心的年纪了,沐浴穿衣这些事儿,如今半点不让娘参与。
封弥的小鸟儿解脱之后,高兴地说:“一定是个妹妹。”
他不但在家里说,走哪儿都跟人炫耀:“我马上就要有妹妹啦!”
果然,两日后,他的妹妹出生了。
“这么丑的吗?”封弥趴在小摇篮旁,非常非常小声地说了一句,他当真觉得丑,可是又怕妹妹听见了伤心。
“臭小子,你出生那会儿像个小猴子,”摇篮旁的赤睦大汗爱惜地抚了抚襁褓,“这会儿脸蛋越红啊,长开了越好看。”
“姥爷,姆姆,你们今日过得好吗?”封弥敏锐地察觉到姆姆和姥爷都有些担心。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