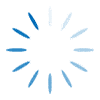便是那前来呈送战报的禁军,亦猜不到自己一语竟能促成这般结果,他立在园外惶惶不安,额前冷汗滑落,城中战事一触即发,他在等一封帝王抗敌的口谕,却不慎卷入了宫闱内乱中,可眼下情形他又催促不得,一时如芒在背。
箭阵中,众人逐渐捉襟见肘,再不复先前游刃有余,赫氏身侧舞姬越战越少,左侧防线凌乱,只右侧霍长歌身法奇诡,将长颈琵琶舞成了盾,屡次救赫氏性命,与她多留一线生存之机。
箭阵外,正有禁军拉扯着丽嫔与连珩要往一旁拖拽,连珩挣扎着伸手,跪伏在地直呼:“二哥!妹妹!”
连珩素来得过且过,从未有这般狼狈时候,连璋于躲避中窥见他这副模样,深知自己与连珣今日难逃一死,见缝插针不由感慨谢昭宁幸好未曾入得宫门之时,又扔下连珣转身便要与赫氏手中抢夺连珍。
光阴往复,旧事回转,合该冤有头、债有主,连珍何其无辜?
赫氏见连璋不顾伤臂出掌攻来,装作不敌就势放手,霍长歌反转琵琶横扫中,装模作样拍中连珍后腰,失手将连珍一个踉跄送往连璋怀中,连璋再反手一推,将连珍送出禁军包围圈,“啪”一下摔进丽嫔怀中。
三人却在此时心意相通、配合无间,甚至不用一个眼神。
谢昭宁远远眺见,一怔间,却是不由牵了牵唇角。
丽嫔失而复得幺女,登时搂紧连珍与连珩抱头痛哭,娇躯打颤中,却仍绝望至心寒——她近身服侍连凤举二十余载,该是比任何人更了解他帝王威仪之下,包裹着怎样一颗奸诈虚伪、寡情薄意的狗肺狼心。
便是今日她与一双儿女侥幸不死,以连凤举多疑心性,来日她母子三人依旧难逃莫须有罪责加身的斩草除根。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注2)
他从未改其鸡肠狗肚的商贾本色,却是他们眼瞎,误认他为明主仁君……
丽嫔于似喜还悲的哭声中抬眸,见连凤举果然眯眸一副起疑模样,她眼底寒芒映着泪光果决一闪,借与连珍疼惜打理鬓发之际,从她发髻间,不动声色拆下一只金步摇藏于袖中。
那原是连珍及笄时,继后亲手赠于她的,危机中一遭来回,却仍稳妥插于她发间摇曳。
她的女儿今日已经很勇敢,眼下,轮到她了……
丽嫔抽噎中,又借着连珩搀扶袅袅娜娜起身,裹挟一身馥郁檀香气息,却在那兵戈交锋声中挺直背脊,陡显铮铮傲骨,便连一副妖魅眉眼,亦在此时显出七分宝相庄严。
“二哥!”连珩半揽惊魂未定的连珍,感念之余愈发记挂连璋安危,他手足无措眺着禁军越收越紧的包围圈,便可见情形越加危机。
赫氏一双淡瞳现出疲色,周身舞姬只战至两人幸存;
霍长歌发髻散乱,覆面薄纱上已印出汗迹,手中琵琶似个刺猬般遍扎箭矢;
连璋手臂伤上加伤,血透重衫,脚下姚氏老少尸横遍地,没剩几个囫囵的,唯连珣拖着伤腿,与南栎不顾身上箭矢,抱着哭闹不止的连璧仍于箭阵下狼狈逃窜。
骤然“啊!”一声凄厉惨叫,却是南烟跪在玉阶之上,攥着连凤举下摆一角,撕心裂肺喊道:“南栎!”
连璋粗-喘之中,循声侧眸,却见南栎挡在连珣身前,胸口中箭,霎时爆出一簇血似的花,连珣一怔之下脚步顿住,又是一箭斜着飞来,正中连珣后心!
连珣“呃”一声闷哼,身形前扑,抱着连璧摔倒在地,额头重重磕在南栎胸前,须臾便没了气息。
南栎平躺在连珣身下,口中溢出大股鲜血,仍挣扎着伸手想去抱一抱他,直着一双点漆似的双眸喃喃道:“殿、殿下……”
连璋难以置信,脚下稍一踉跄,便不忍别过头去。
谢昭宁深深动容,下意识提刀探出半步,却闻太子哆嗦着唇念出一声:“阿弥陀佛。”
“啊!五弟!”连珍抹着眼泪哭道。
“珣弟!”连珩人群外窥见此景,惊呼一声,那箭阵便在此时缓了一缓,禁军众人不由侧眸去瞥连凤举,却见他并未有半分不忍,抬手一挥,仍一字一顿、掷地有声道:“继续!”
那嗓音中沉着的寡情,冷得周遭转瞬由夏入了冬,寒得人心也凉彻底了。
霍长歌得这一时喘息,合着南烟的惨叫声,下意识转眸探过身前身后,漫天箭雨下,半座御花园早已为鲜血所浸染出一副人间炼狱景象,不由戚然。
她眼底陡然似有血光浮动,恍惚瞧见前世盛夏的辽阳城,到处堆叠了尸体在焚烧,气味腐朽腥臭,遍地跪着人在恸哭哀嚎,浓重的乌烟汹涌翻滚、遮天蔽日,在城内持续盘桓,似一面巨大的令人绝望的招魂幡。
她似又看见深秋的辽阳城,城门已破,玄武军灭,百姓俱亡,到处血流成河,散落一地残肢断骸。
大年初一夜里,连凤举那句“莫伤百姓”,如今看来,也不过一场笑话。
她从未误判过连凤举的绝情,低估过他的狠辣,他早已端坐于皇位之上无情俯瞰世间,欲肆意将众生玩弄于鼓掌中,没心了。
躲不过了,今日之始,便要种下来日北疆的果,姚家古家尽除,连凤举再要做甚么便谁也拦不住了,光阴轮转终要回归那末路去。
霍长歌于那层层叠叠的人墙缝隙间,又留恋似得去眺那玉阶上隐在禁军中的谢昭宁,他不知何时起,已挪至皇帝与太子间的夹角处,手持长刀微微颤抖,回望她时,眸中温情敛着遗憾,便如正西落的夏阳。
跨过这一步,他们便能回到北地去,只这一步太难走,他们终究要到不了了……
倏然,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大地再度震颤,天旋地转中,列阵禁军身形一晃间,破绽尽出;弓手亦难以瞄准,射而不中!
霍长歌眼神陡转锐利,她蛰伏许久,待的便是这一刻!
熟料,谢昭宁似也在等这个时机,竟手中提刀渐起,像是要趁乱架向连凤举颈间!
霍长歌惊骇之下,眸中决绝裹挟歉疚,她前世便愧对他许多,今生若由他出手,便要彻底赔上他生父谢翱的声名,再无转圜。
霍长歌扣着丝弦的手指稍抬,与赫氏匆忙打了“以身献祭”的暗语,她中指与拇指伸长一并,其余三指稍抬做飞羽状,便是所谓的“凤凰浴火”。
她赌皇帝便是死于她手,谢昭宁助连璋夺位后,亦会妥帖处置她尸首,不至于令她声名外露,累及霍玄与北地三州——到头来,霍长歌便可得圆满,她早已死于庆阳前朝别院的那场大火之中,从未入得中都来。
这局棋,终要落下最后一子,只她到头来,又要辜负谢昭宁,唯辜负谢昭宁而已。
赫氏已累到疲乏,只凭一口怨气吊着精神,窥见霍长歌指间暗语,眸色一凛露出嗜血模样、精神倏得振奋!
赫氏与身侧那俩舞姬亦打了手势,借霍长歌横舞琵琶放出最后一把天女散花式的银针替她遮掩之机,她十指分往左右腰间利落一抹,指缝间便各挟三支梅花钉,她韧腰再一拧间,霍长歌探指与她腕间加力一震,“咻”一声,内劲裹挟旋转之力,致使六支梅花钉骤然脱手,角度刁钻得直朝连凤举周身射去!
那六支梅花钉去势极快,两股力道加持下,银光绞着垂落夕照登时飞得眼花缭乱,轨迹竟难以尽数捕捉,连凤举并着身侧禁军一时反应不及,那毒钉便已到眼前,丽嫔亦正在此时脚下突然站立不稳,一副惊惶模样便踉跄朝连凤举合身扑去!
谢昭宁瞥见霍长歌翻转琵琶便与她生了同样念头,心知她怕要起了协助赫氏弑君的心思,已不及怪她违誓,只恐此举牵连霍氏,并着肩负忠君的职责,先一步执刀越出队列,抢在那毒钉前一把拉开丽嫔,旋身横刀飞舞“叮当”挡去数枚梅花钉。
合着那数声脆响,丽嫔摔在连凤举身旁,袖中金步摇悄然滑落,掉在玉阶之上。
那银针打的是禁军,梅花钉亦不过是迷魂阵,非是冲着连凤举而去,封的乃是其周身守卫大穴,阻的是其救援的进途,谢昭宁心道不好,果不其然,只这一息功夫,霍长歌已掉转琵琶,借银针余威,将身前禁军人墙砸出一道裂隙,趁机抓住赫氏腰间缎带,将她一把掷了出去!
电光火石间,禁军不待反应,便见赫氏已凌空飞跃而来,左手再射三枚毒钉直取连凤举面门,右手两指间挟一泓秋水似的刀刃,拖着腰上长而飘逸的缎带,似仙女临凡般骤然落到连凤举面前,抬手便刺!
谢昭宁翻腕横身再挡暗器,逆着刀势却不及回防,不由合身扑在连凤举身前,硬接了赫氏那致命一刀。
那刀刃薄而窄,似一截寒冰刺入胸前,起初只觉冰凉刺骨,一息后,方才有针扎似的痛感席卷而来,好在他中刀之际,左手及时握住刀刃,带得那刀尖偏移了一寸,擦着心脉要害倾斜刺入。
“你——”赫氏一眼认出谢昭宁来,却是两指挟着刀刃并未松劲,一双淡色的眸子怨毒而茫然。
纵然他欲逼迫连凤举罢手,却是代行正义之举,他父其人豁然通达,身后虚名不比活人性命,与古氏、霍家生前更是知交,想来不会怪罪于他;但当值一日,便要尽忠职守,他万不能坐视不理——
谢昭宁掌心亦被那锋利刀身切开两道刻骨的伤,鲜血滴滴答答自那刀口成珠似得缀下,呼吸间,胸前伤处又疼得他身形微见佝偻,已说不出话来,颤抖双唇与赫氏沉默四目相对时,赫氏却似读出了他未言出口的诉说。
……愚蠢!愚蠢呐!
只这眨眼功夫,连凤举周身禁军已反应过来,举枪便攻,赫氏复又错失良机,恼谢昭宁多管闲事,眸中怨毒大盛,左手于腰间一抹一抬,携最后三枚毒钉挟滔天恨意便欲再射连凤举,却被谢昭宁反手以刀背削她手背。
赫氏愠怒气苦,就势便将那梅花钉狠狠按在了他肩头。
谢昭宁闷哼一声,吃痛却不松手,赫氏拔不出刀刃,便右手两指发力,狠心捅得更深,将他堪堪钉在连凤举身上时,却见谢昭宁腕间一转,近身一计横劈险些将她拦腰斩断,他留情刀势一顿,另一手血掌半抬按在她胸腹间劲力一吐,只将她倏得震开。
赫氏后退几步便又撞上禁军人墙,不得己纠缠之下,仍不死心几番挣扎欲上前刺杀连凤举。
她赤手空拳又杀红了眼,丹田受创,出招也受阻,周身皆是破绽,后背冷不防便挨了一刀,不禁喷出一口鲜血。
霍长歌携她舞姬正自那强行撕开的人墙裂隙间杀出来接应,见状飞身上前护她,一掌托住她后腰助她稳住身形。
“我不能败,咱们不能败!”赫氏歪靠在霍长歌耳侧,气息阻塞间,自喉头滚出一句沉重而绝望的咆哮,“去杀了他——”
隔着半堵禁军人墙与七步距离,谢昭宁骤然与霍长歌打了个照面,他额间冷汗涔涔,呼吸重而乱,胸前插着半截刀刃,肩头毒钉处已渗出紫黑色的污血,形容狼藉中,却仍与她温柔笑了一笑。
那一笑短促而清浅,愧疚中又分明裹挟壮士断腕的决心,他不顾霍长歌边横舞着琵琶护着赫氏边含冤狎怒瞪他,正要提刀转身,却从霍长歌遽然睁大的眸底意外得见他身后,南烟自玉阶上悄然摸到了一支金步摇,电光火石间,奋力跃起,一把将其狠狠插进了连凤举颈间!
谢昭宁回身尚且不及,一捧鲜血霎时绽开在他脸侧,温热湿滑,沿着他脸颊缓缓淌下来……
第66章 枷锁
禁军下意识停手, 众人骇然而屏息,一时间,似人人皆能闻见鲜血滴滴答答滴落玉阶的声音。
周遭霎时一片死寂, 半晌后,连凤举身后那大太监方惊慌尖叫:“陛下!”
禁军这才如梦初醒, 无意识出枪, 南烟胸口骤然透出半截枪头来, 她吃痛闷哼,不由缓缓松开紧攥在手的金步摇,“咚”一声跪扑在地,却仍挣扎探手,扯着连凤举龙袍下摆,口溢鲜血喃喃道:“陛下答、答应饶南栎一命,送我们姐妹俩出、出宫去……可你杀了南、南……”
话未说尽, 人便横倒在玉阶上, 断了气息。
连凤举瞠目瞪着虚空,竭力张口艰难喘息, 像是一只缺水的鱼, 他喉头不住发出痛苦的“嗬嗬”声, 颈侧伤处又迸出大股大股的鲜血。
那步摇没入极深,只余一只衔珠的凤凰露在颈外, 随连凤举奋力呼吸而轻轻摇曳, 映着夕照晃出一道微弱但璀璨的流光, 他两只手在半空胡乱抓挠,整个人剧烈颤抖, 眼看便要站不住。
“父亲!”太子惊愕滞住一息,猛得爆出嘶声裂肺的呐喊, 他扔下手中佛珠,推开众人踉跄奔来,伸手扶住连凤举后仰身体。
谢昭宁正在此时转过身去,心中一瞬惊涛骇浪,他睁圆一双凤目,未及体会胸腔内那团似被遽然塞进的满满当当又纷繁复杂的情绪,顶着半脸的血,只下意识向前倾身,与太子一左一右接住连凤举。
“叫太医!去叫太医!”太子歇斯底里大喊,面容因惊骇而扭曲,眼角聚起恐惧的泪水。
在场禁军怕有三千余,一时杀得兴起,不察竟让一个弱女子钻了空,连凤举若是遇刺身亡,眼下当值之人怕皆要以渎职论处。
众人心有余悸收招,持枪正面面相觑,闻言似幡然醒悟一般,“呼啦”一声,不少禁军并着宫婢拔腿便往园外跑,争先恐后要去请太医,围攻之势顿时瓦解,人墙渐渐松动,隐约透出缝隙。
“站住!无令妄动者,杀!”都检点见状一声爆合,须发喷张,长枪杵地发出震慑似得巨响,脱队禁军与宫人便又茫然转身回来,“眼下外乱未平,即刻封锁内院消息!若有泄密动摇民心者,三族尽诛!”
都检点雷霆下令,又拨开众人上前,俯身往连凤举颈间探查伤情,怛然失色下,却是亲自点了一队人马飞快去往太医监,自个儿转而守在太子身侧,眼神复杂眺向园中乱象,竟为难拧眉。
“南晋皇帝……是要……是要死了吗?”赫氏那两名舞姬已战至乏力,周身攻击遽停之下,却是不敢置信般从那人墙缝隙中定睛探去。
“公主!哈哈哈哈公主!”其中一名舞姬突然仰天大笑,“皇帝要死了,皇帝真的要死了哈哈哈哈!”
霍长歌一手仍托在赫氏后腰,二人亲眼目睹南烟那掣电一击,竟半晌回不过神来,恍如置身梦境一般——她们花了那许多心思、费了那许多功夫,前前后后又搭进去许多人命,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局?
霍长歌目光复杂得凝着横死玉阶之上的南烟,不由忆起永平宫中许多旧事来——那也是个心善的姑娘,便是叛主也叛不彻底,处处要露出马脚与她知晓,生怕她也陷落帝王权数的阴谋中。
谁又能料到,连凤举治下的苦主众多,他竟会毫无防备死于这样一个人的手中——一个恐在其眼中,卑微渺小似草芥一般的人物?
真是可笑又可悲……
只,谁又更可笑、谁又更可悲呢?
霍长歌心中那根弦,却在此时崩得越发得紧,愈加审慎起来,凝神留心周遭——浮图七级、重在合尖,如今才到真正关键时候,她万不能功亏一篑!
霍长歌身后,连璋正旁若无人似得跪在连珣尸身前,掌心竖着一抹,助南栎合上一双不曾瞑目的黑瞳,又沉默搂着嚎啕大哭的连璧不住拍背安抚,他似转瞬回到了五年前那天飘细雪的料峭晚春,便是此时肩顶艳阳,仍觉冷得厉害,身子微微打颤。
茫然间,周遭局势又起变化,待连璋闻见太子那惊天动地的一声,抬眸呼吸一滞,单手抱着连璧缓慢起身,于禁军注视中坦然前行,竟无人阻拦。
连珩余悸犹存,扶着连珍亦往连凤举身前踟蹰过去,途中搀起摔在阶下的丽嫔,转眸便见连凤举颈间那似曾相识的金步摇,迎着夕照“叮当”乱跳。
连珩:“……?!!”
连珩压着惊惶,不漏痕迹瞥过连珍发髻,再不动声色对上丽嫔沉着双眸,反手便将连珍又掩遮在了身后——那金簪原是及笄时,皇后送给连珍的,却因丽嫔起了杀心而有了旁的用途。
为母则刚,那是一个母亲的决心。
恍然间,似平地卷起微风,连璋也顿足停在了连珩身侧,与连凤举血脉相连之人,此时俱在阶下齐聚,却不约而同皆不愿再上前一步。
玉阶上,连凤举躺在谢昭宁与太子两臂之间,禁军与虎贲卫在其身后叠了三层有余,众人凝神屏息,一片死寂中,只见连凤举眼皮颤抖、嘴唇翕合,紧紧握住太子另外一只手,聚眸死死盯着他,似有千言万语想要交代,几番挣扎下,拖着沙哑嗓音,却以一个“杀”字艰难开头:“杀——杀——”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