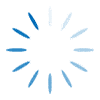“城西城南城北,关卡已架设完成。”
“城东驻军已将百姓聚众保护,并加派人马把手城门,严防前朝遗民与山戎里应外合,趁乱开门投敌。”
“城西城南,弓手就位。”
“城东城北征得豆油与烧酒。”
“城东炮房中的存余,已运往城南与城西。”
“……”
再过得片刻,陆续又有人来呈上战报:
“敌军投以巨石开道,同时攻袭城西、城南、城北。”
“城西城防损毁已近七成。”
“城南城防损毁已近八成。”
“城北城防损毁已近五成。”
“城东捕获二十三名前朝奸细。”
“城外暂无援军踪迹。”
“……”
合着远处不绝于耳的轰鸣,刻漏缓缓上浮,屋内越发昏暗,苏梅自隔壁屋中点了油灯捧了来,却见霍长歌身前沙盘中已变了一番模样——半数城防被她推倒,尽显疮痍。
*****
亥时七刻,月挂枝头,银辉尤显清冷肃杀。
暑气已渐消下去,窗口隐隐飘来艾草的苦涩清香。
素采匆忙跑过半座庭院,推门进来:“小姐,城南城防即将坍塌,城西尚有一分余地,但城破不过片刻功夫!”
“着三殿下按计划行事。”霍长歌负手立于原地,整晚一步未动,闻言一把推倒沙盘中的城南城墙,先偏头镇定从容与素采交代了,方又转而与苏梅眼睫淡淡一挑,“带着你的人去城西帮扶二殿下,莫让他死了。”
嗓音清而稳,未因中都提前沦陷而慌乱。
“是。”苏梅应声转身。
*****
城南,那屹立千载的中都城垣,裹挟在熊熊烈火之中,已被灼烧了半日,眼下又被巨石由外砸出几近绝望的哀鸣,尤显无助与悲壮。
城上站不得人防守,城下又烧出一片火海,难以靠近,寻常攻守法子便已行不通,遂霍长歌着谢昭宁大胆召回守城军,又与禁军一同撤回城内,将三千人马重新布防,守住关键要塞。
倏然“哗啦”一声巨响,城门上方墙体被巨石豁然洞穿,土块四射飞出,两侧砖石不住崩落。
终于,以铜浇筑的厚重城门失去支撑,轰然声中向内“哐当”倒塌,似巨人临死前发出的咆哮,撼天动地。
城前扬起漫天灰尘,与浓烟交织,遮云蔽月,天地间骤然一静后,又倏起震天战鼓,一声催着一声,直将三千山戎骑兵推入城内。
刹那间,群马嘶鸣,脚步杂沓,山戎人结了小队,悍然自半条仍在燃烧的街巷中勇武冲出,沿着宽阔笔直的官道打马疾驰,狂声呐喊。
沿途两侧房屋顶上影影绰绰,似暗地伏着不少兵马,山戎骑兵果决张弓漫射,“叮当”声中,似射中了头盔之类的硬物,却不见有人中箭哀嚎坠落,迟疑间,身下奔马便猝不及防撞上贴地拉起的绊马索,霎时摔得人仰马翻,更与后继骑兵接连相撞。
人声鼎沸,马匹哀鸣,山戎出师不利,慌乱之中竟未觉察自两侧屋檐上“滴滴答答”淌下了不少豆油。
谢昭宁远远伏在一侧民宅屋顶之上,见状一挥手中湘叶黄的小旗。
不待山戎士兵驱马翻身而起,又自两侧屋顶上倏然滚落许多瓷罐,“稀里哗啦”摔落余下半条街巷,散出浓郁酒香。
“唰”一声,烧酒贴地流淌,引着四处散落的火源,“轰”一下复又茁壮蹿起。
火苗更舔着墙壁豆油,一路攀爬至屋顶,织成无法逃脱的囚笼,再迅疾接起城前大火,点燃大半城南。
只眨眼功夫,那坐卧于屋瓦之间吞吐赤火浓烟的狰狞巨兽,似被再度唤醒,张牙舞爪追在山戎身后,一口将其吞噬。
山戎躲避不及,陷入烈火,凄惨哀嚎。
沿墙角铺了薄薄一层的枯草下,埋着的炮竹亦被引燃,“噼里啪啦”炸响声中,马匹骇然受惊,发疯似得旋身踩踏,随即火海里更有山戎骑兵抱着伤处倒地痛呼悲鸣。
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誓在今日以牙还牙。
敌军先锋铩羽,似无头苍蝇般得逃窜,慌乱中又撞向两侧民房,周身再沾豆油,愈发绝望。
城南一时恍如白昼,哀嚎之声不绝于耳,合着鞭炮欢快而清脆的声响,讥讽而狠辣。
中都街道四通八达,山戎后方人马见状避开主路,转而往小巷散去,却不料狭窄小道更暗藏玄机——纵挖的陷马坑里遍竖锋利铁棘,便是在等他们拿命填。
接连惨叫声后,只片刻功夫,暗巷中也没了动静。
山戎第一轮冲锋,竟悄无声息便折在了城门前。
谢昭宁率人遥遥守在巷尾,审慎远眺,只见火海铺陈半座南城,焦黑躯壳遍地,再静待须臾功夫,又一声沉重擂鼓,马蹄复又踏响大地,他身侧瓦片簌簌震动嗡鸣。
陡然,又是一队山戎骑兵狂声呐喊跃入城门,冲进火海,以人命勇猛开道。
谢昭宁冷静再挥手中小旗,屋檐两侧数千禁军“唰”一声齐齐张弓,寒芒汇成漫天箭雨,瞄准火墙尽处。
不断有骑兵精锐周身焚火冲出火墙,再惨叫中箭倒下,尸身叠着尸身,血河不及流淌便干涸渗进泥土。
残月在杀伐中缓慢爬上中天,无情俯瞰惨烈世间。
几轮箭雨之后,禁军已轮番射空箭囊,却仍阻不住山戎人源源不绝闯入城南,踩着同袍残躯铺就的通途,突破重重关卡,冲出巷道,直直撞上长街尽头守城军以盾牌与肉身筑起的层层人墙。
双方终于正面交锋。
“杀!”谢昭宁扔下手中小旗,大喝一声拔剑率众自屋檐扑下,左右夹击敌军残部。
他手中正是武英王那柄子剑,剑锋锐利划过异族脖颈,鲜血与月光流淌于剑身之上,又暖又冷,泾渭分明。
这是他的城——谢昭宁矮身避过骑兵自马上刺出的一枪,就势挥刃雷霆砍断马腿,再起身反手一剑刺穿骑兵后心,鲜血霎时溅落在他胸前——他从未一刻有过这般强烈的感受,这是他的城,纵他心心念念远去,亦不容外人践踏。
备战布局之时,他带人清理城前街巷,方知只短短两个时辰,便有多少无辜百姓受此无妄之灾,其中更有武英王府邸前那日复一日卖了几十年粽子的阿婆,白发灼得齐耳,四肢焦黑扭曲……
谢昭宁下手愈发利落,剑锋于身前划开冷冽白弧。
撼天喊杀声中,涌入城中的敌军越来愈多,无情冲撞着城南防线,禁军已杀红了眼,却是守在盾阵前一步不退。
“轰隆”一声,远处传来熟悉巨响。
谢昭宁率众数次冲锋,卷在阵中身先士卒,难免牵动伤处,便心知霍长歌所料不假,此番山戎尽是好手,若非前个时辰布阵耗去他们半数人马,恐更要恶战。
谢昭宁不住旋身挥剑杀敌,闻声又担忧远望城西方向,散乱鬓发倏得一荡,便似觉察出甚么来,长眉敏锐一蹙。
他拼杀中间隙一眺,果然便见身前火海正朝东北方向明显蔓延飞卷,不由一怔。
“副将!”谢昭宁迅速权衡眼下局势,果决杀出重围,忙喊了人来顶上他位置,随即寻了敌人空马翻身而上,往燕王府飞奔过去,披风荡起弧度。
*****
谢昭宁飞身下马,入了府门险些撞上步履匆匆的素采。
二人先后奔至霍长歌厢房。
“长歌——”
谢昭宁眼前眩晕一瞬,身形一个踉跄,下意识扶住门扇一顿,素采便抢了先,急急冲进去与霍长歌道:“小姐,城西陷落!”
霍长歌于沙盘前闻声回首,见状骇了一跳,忙先去搀了谢昭宁于桌旁落座。
昏黄烛火下,谢昭宁面色憔悴,额前冷汗涔涔,手指冰凉。
银白轻铠上更结了厚厚一层血泥,周身浸染焦腥气息。
“三哥哥?!”霍长歌探手便要去掀他领口,急道,“可是又受了伤?”
“未曾,只牵动了旧创,不妨事。”谢昭宁缓过一瞬,已好了许多,按住她手便抬眸略有焦急道,“眼下起了西南风,怕是不久要落雨。”
霍长歌不由一怔,诧异反问:“中都端午时节,竟会落雨?”
“是。”谢昭宁认真答她,“西南风起,电闪雷鸣,滂沱白雨来得疾,去——便怎么也得两个时辰后。”
“落白雨?!”素采亦在一旁惊道,“盛夏少风,咱们战术如今皆依托火攻,若是改了风向又变天,怕要不好!”
“城南情况如何?”霍长歌却是沉着先问谢昭宁。
“备战充足,”谢昭宁冷静回她,“可守。”
“想来主帅未入城南?”霍长歌了然道。
谢昭宁摇头。
“亦未入城西。”素采自觉跟答。
“城北眼下如何?”霍长歌又问素采。
“……损毁近七成。”素采稍稍一顿,便嗓音脆生生得又续道,“城南靠山,城北依水,巨石运送城北不易,攻袭力度便不及城西,亦已有所减缓。”
“那他只能入城西,就快了。”霍长歌闻言转眸却道,“西南风一起,那火便要烧到咱们自己,亦与抢攻城北不易,草原人更熟稔气候与风向,须臾便要觉察,便不会再攻城北了。”
“可要抽调城北驻军往城西支援?”谢昭宁道。
“抽。”霍长歌同他点头,略一沉吟,与他正色道,“咱们变,山戎亦会变,这雨‘害我而利他’,一旦落下,便要失军心,故——”
她话未说尽,陡然一道青紫电光骤然映亮半个厢房,继而一声雷鸣,重如天神擂鼓。
三人闻声侧眸。
“糟了!”霍长歌疾步推开窗扇,瞠目一望,便见一条刺眼电光在云端起初若隐若现,不过眨眼功夫,便已漫天织成银白色的蛛网,兜头劈声砸下,“这也来得太快了……”
谢昭宁见状愕然,扶着桌面不由起身,手臂微微颤抖。
“三哥哥,你速回宫中。”霍长歌伏在窗前,眼瞳微颤,缓过一息便转身挑眸沉声,合着窗外飘入的潮闷气息,果决道,“素采,通知城北驻军变阵,再着人将城南骁羽营卫尽数调出,随我去城西。”
“好。”谢昭宁道。
“是!”素采应声。
*****
城西,霍长歌原设下相似布局,连璋远远手持小旗守在巷尾,但山戎显有防备——先锋闯出火海,便伏于马背,拖着曳地长刀,“咻”声中斩断路间贴地拉起的绊马索。
幸而城西战法有变,沿途十步一个高栅栏,看似堵了路,而栅栏间却是上铺了枯草遮掩的陷马坑,坑中又竖了尖利铁棘。
待山戎跃过高栏,便连人带马摔死在坑内。
禁军等在街巷两侧墙后,见状便往那坑中抛出酒罐和油桶,一支支火箭再远远射来,依葫芦画瓢渐次点燃大半城西,完成对山戎的首轮阻截。
紧接又有大队山戎骑兵骁勇入城,火海之中众人合力以长枪掀飞高栏,又无畏踏进坑道,以血肉之躯填平沟壑,为后继同袍开道。
而第三波冲出巷道火墙的山戎人,却在禁军漫天箭雨截杀中,引弓射出火箭反击。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